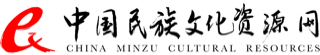传统与时尚交融中的民族特色服饰——来自黔西南小城的故事

令人目不暇接的剪裁、成衣都是经验的体现。

头顶悬挂着制好的衣服,裁缝阿姐手上开始测量下一件的尺寸。

蓝色的手是以蓝染为生的人重要的标志之一。

搬进城中安置房后,在阳台上依然制衣的妇女。

黄奶奶帮我穿戴布依族的服饰。

黄奶奶在织布。

黄奶奶在染布。

隔着蚊帐看到正在绣花的黄奶奶,一切是如此温柔。
2020年春天,我投宿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九万大山中的一位壮族舅娘家。她开口第一句话就问我,衣服是哪里得的——我穿着民族特色衣衫。
“你觉得好看吗?”“好看!我们以前也会做,现在忘记了,会做的人都找不到了。”
我意识到,传统的“消失”并不等于“不被需要”,有时只是慢慢“不被看见”“无法找到”。我答应下次给舅娘带两身衣服。
秋收时如约再去,舅娘刚干完一天的农活,浑身汗湿,等不及洗澡就换上新衣,打着手电筒,乐颠颠消失在我们面前——出门去找好姐妹了。果然,隔天村里就有阿婶和我说:“我们好喜欢这个衣服。”
那时,我就决定要回到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3年前买到这几件衣服的地方,去了解现代生活中民族特色服饰的故事,探究传统与时尚碰撞交融之下,民族服饰的未来之路。
1 苏阿姨的裁缝店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每周一次的集市,是方圆几十里山山岭岭、沟沟谷谷乡民们的盛会。野菜、山果、草药、竹编、花米饭等小摊沿着穿过县城中心的河流一排排支起,随处可见背着竹篓、穿着传统民族服装的女人们结伴赶场。
集市附近是一栋栋天地楼(盛行于县镇级和城中村的多层住宅)连成的老交易市场,里面隐藏着十几家裁缝店,专门定制本地常见的偏襟短衫。每家经营的侧重都稍有不同。3年前注意到苏阿姨家,是因为她做的衣服素雅古朴,不是大花大色的舞台风格,而是用蓝、灰、青、月白等色,或是缠枝纹、鱼鳞纹、圆圈纹这些古朴纹样的布料,没有多余缘饰,显出衣服结构本身的古典美。不过这次来,她的面料明显鲜亮起来,纹样也更趋现代。
“为什么不卖以前的纹样了?”“大家喜欢现在这种,我也要看新的流行样式。”苏阿姨抬头回答,手上的动作也不落下,“颜色亮,布料上花多、花大才好看。”
她是店里的老板,也是唯一的裁缝,多艺能干,丈夫只是从旁协助。她说母亲是村子里的裁缝,从小就耳濡目染,十几岁决定以此为生,“年轻时精力好,把衣服做好后,到处赶场卖。”
贵州很多地方至今保留赶场的风俗,相邻地方的日期往往会错开。“只要肯干,一年365天都可以开张做生意。”苏阿姨回忆年轻时一天可以做几十件衣服,忙不过来还要分出去一些请人做,直到年纪大了,才在县城租下门面。
苏阿姨做衣服用的化纤面料,穿起来垂坠有型,可是时间一久我就发现它不透气也不贴身。我试图和她讨论使用棉麻面料的可能性,没想到她一听就拒绝了。
“为什么不用棉麻呢?” “大家不喜欢。”“为什么?穿起来舒服呀。”“不好看。”“不好看?”“容易起皱。大家喜欢不起毛、不起皱的面料,喜欢穿起来齐整、几年都一个样。”
这不仅是苏阿姨一个人的做法,我逛完当地所有的裁缝店,也很难找到一家用棉麻的,大家给出的理由大同小异。后来认识几位返乡创业的年轻人,才知道望谟县还是有人用自然面料做传统民族服装的。在她们看来,很少人使用自然面料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价格。创业青年们的用料好,设计也在传统基础上有一定创新,成品价格少则几百,订制则要上千,这显然是县城中一般妇女难以消费的。
走在望谟县的路上,所见大部分是中老年人,以女性居多。我经常看到老人用背带背着小孩缓步前行,等她们走过去后,我会仔细看一眼背带上的花纹。大多从农村来县城的老人是“来带孙孙,陪孙孙读书”,而她们恰恰是穿着传统服装的主要人群。
我逐渐理解了像苏阿姨这样花费100多元就可以订做一套衣服的店铺,它提供了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选择。事实上,每天来苏阿姨店里订做衣服的也都是这些阿姐、阿奶。她们有的结伴而来,有说有笑,有的订完衣服仍坐在那里聊上半天,也不赶时间。
有时发现我在拍照,她们会害羞,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自己老了,拍照不好看了。我就趁机多问一句:“为什么现在这样的衣服年轻人过节才穿,你们每天都要穿呀?”“穿惯了,不能脱了。”她们笑笑回答。这种传统款式,裁缝们称为“父母装”,很现代的说法。
订做讲究量体裁衣,苏阿姨有个小本子,专门记录客人的身量。上面能看到衣长、腰长、袖长、领长和住址,可唯独不知道她们真正的名字。布依族女人的名字,一生都在变化。婚前的小名,一旦结婚有了孩子就变成“妈”加长子(女)的名字。等做了奶奶,又会变成“奶”加长孙子(女)的名字。我仿佛看到她们把自己越缩越小,隐身在家庭之后。
在苏阿姨的店里待了几天,我也慢慢会看着人猜测大概尺寸,不过总有些和我估算的不一样。“年纪大了,身体会有很多变化,像是驼背。”苏阿姨解释,对老人来说,穿着舒服更重要。她们喜欢宽松,所以通常会做得更大。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很多阿奶来,直接拿一件衣服请照做,那是她们平时穿惯的尺寸。“年轻人的就要裁准确一点,可以更好地显出窈窕身型。”好裁缝不仅是手艺,也是眼力和经验。
最后一切都要落在裁剪上。没有固定的图纸比照,每一件都是新尺寸。苏阿姨把面料对折两次,用尺子横竖测量,画出交错的直线和曲线,沿画线剪开,提拉,再画,再剪,再一打开,衣身就变戏法似的出现了。和现代服装前后衣片分开缝在一起不同,这种方式裁剪出来的前后身一片相连,只要侧面接上袖子,衣服就大致成型。整个过程目不暇接,最后呈现的结构又如此简单。我眼前这一幕,是在无尽的沟沟岭岭之间,经历了无数日月交替、秋染霜丝才成就的场景。
2 染布的黄奶奶
我依然没有放弃寻找本地自然布料的想法。
第一次在路上遇见黄邦芬奶奶,直觉就告诉我,她是我一直想找的人。一开始被她吸引,是看到提着一袋酸菜和一袋米豆的一只被染成蓝色的手,视线再往上,果然,看到了一位穿着黑色蓝靛土布大襟的老人。
“是您自己染的吗?”“对。”“染缸在哪里呢?”“在我家楼顶上。”
她安静地注视我,眼神有着超出常人的清亮,脸上散发着珍珠一样的柔光。只说了几句,就同意让我跟她回家。
穿过几条街巷,她家是五六层高的楼房,充满怡然自乐的生活气息。楼顶养鸡种菜,一只白色的土狗叫唤累了就躺在腊肉架下的阴凉里休息。从地面抬高垒起、因地制宜的火坑,是厨房和整个家的灵魂所在,火烧起来时,叫人忘记身处县城,瞬间飞回那个红水河边优美宁静的村舍。
黄奶奶的儿子叫江生,他告诉我,他们老家在望谟县城60公里外的昂武镇,背靠大山,门前有条大河流过。翠绿绵延的河山长久地滋养着两岸的布依族人,直到十几年前修建水电站,淹没了土地和村庄。
“我觉得以前老家的生活更自由快乐。”还没等我发问,沉浸在回忆中的江生说。突然间我就明白不需要再问黄奶奶:为什么你依然穿着土布?依然自己染衣?
黄奶奶的房间堆着好几箱土布,都是给孙子孙女准备的。有些是从老家带来,有些是到望谟以后再织再染的,一卷布要做几个月,一年一年积攒才有这么多。“以前出嫁,都要抬这个布去。”黄奶奶说。
望谟县布依族的土布按用途和制作工艺大致可分为两种:纯色布与格子花布。前者是先把棉线织成白布,然后放入染缸,染成深浅不同的蓝度。布依族尚黑,老人爱穿黑衣,显得庄重,年轻人一般穿浅一点的蓝色。因为是贴身衣物,质地相对细软。格子花布则略厚韧一些,要先将棉线染成深蓝、中蓝、浅蓝、灰、深灰、青等颜色,再上织机织出不同的格子纹样,也有做条纹的。这种布通常需要五幅拼在一起做成床单,夏天躺上去,尤其是在通风性没那么好的水泥楼房里,就像睡在竹席上一样清爽,一整夜都不会湿汗,同时又没有竹席的冰凉。等到冬天,它又暖和贴身,十分好睡。另外还有一种妇女用来包头的格子布,摸上去软和些。
布依族传统棉被由被里、被胎(棉花胎)和被面三部分组成。黄奶奶会用一种纯色的蓝布做被里,被里上面放棉被后,卷折四角,再铺上被面缝在一起。贴身的被里讲究舒服,用土布舒爽透气,不会湿汗,有蓝靛的香味。
我在黄奶奶的房间里发现着土布的日常用途。这些土布或任何传统物件,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们才能“活过来”,展现生命力。
最特别的还要属一种介于纯色和格子之间的布,乍看是纯蓝,仔细瞧里面又藏着深色的细条纹。追溯起来,黄奶奶先染蓝线,和白线一起织成布匹,才放入染缸中染色。用这样的布裁衣,有一种低调的华丽,仿佛不经意间透露出主人的爱美之心。
黄奶奶带我去看她染布的地方,屋顶一间小小的屋子里摆了三个大缸,还没走近就闻到浓烈的蓝靛发酵所产生的独特气味。染缸用厚厚的布盖着,如同黄奶奶的秘密宝箱,要掀开才能看到里面深色的液体。“今天不成,下次染布给你看。”她看了看液体表面,也没多说,似乎染缸有它自己的节奏。
后来,我好几天都到黄奶奶家,希望她可以染布给我看,但似乎总是机缘不到。一天,在黄奶奶家午睡醒来,隔着蚊帐,看见她侧对着我正在绣花,沉浸在一片温柔的光晕里。那是黄奶奶的另一项手艺,绣有龙凤、狮子、蝴蝶、花朵、螃蟹这些吉祥花纹的绣片,会用在小孩背带上,保佑他们健康长大。家里每个出生的成员都受到美和爱的环绕。
黄奶奶的孙女灿烂先前就从橱柜翻出家里所有的背带给我看:刺绣、拼布、贴片,不同的工艺,留下不同时代的浪漫。那种爱和美的生机,仿佛能穿越时空,让人感受到缝制时的心情。
当我们讨论以前除了背带,还有哪些地方会用到刺绣时,江生说他小时候睡的枕头更精致,绸面上用丝线绣着各种美丽的图案。黄奶奶从柜子里找出半床“单辅”(音),它是铺在土布被单下面的一层,上面会绣满花草鸟兽,边缘手编的流苏随着床沿静静下垂,好看极了,这是很多年前大女儿手工编织的。在传统的布依族人看来,即便是铺在被单下、睡时完全看不到,也要绣得美好,因为它代表了绣娘的心意。以前,白色的“单辅”大多数时候都要蓝染过,这样睡在其上才有清香。这也是布依族人不计成本的浪漫吧。
隔两天在约定的时间再来黄奶奶家时,终于看到了染布。“怎么染呢?”“不用讲,我染给你看。”
只见缸中漂浮着蓝色蘑菇状的泡沫,中间不规则的隙孔像是在呼吸。一旁的灿烂觉得好玩,找来一块布条想放到染缸里,被拒绝了。“不能用脏的布,要保持清洁。”黄奶奶正声说。
在这之前,我以为蓝染就是把布料直接放进缸里,浸泡一会儿,再捞起来晒干。可实际上,古法蓝染的过程中需要反复浸泡。由于布料长有十几米,黄奶奶先得一一理顺,才拉成折叠形,一叠一叠推进缸中。她神情肃穆,像是进行某种仪式,周围的空气也跟着沉静下来。一个小时后,黄奶奶依然一叠一叠像鱼尾拍打水面那样捞起布料,但捞出时布料的颜色并不是蓝色,而是一种黄绿色,它在接触空气的刹那像获得了某种力量,缓缓变蓝。这是氧化还原反应。
“染好后,颜色会掉吗?”由于过往体验,我对蓝染的稳定性存有怀疑。“好的黑布,要反复染一个多月,做出来的衣服再洗就不容易掉色。可能开始掉一点点,洗两三次后就不掉了。”黄奶奶笃定地回答。
“每天这样染,持续一个月?”我不敢相信。“而且一天要染三次哩,隔三天又要洗一次,晾干了再染。”“洗的时候颜色不会掉吗?”“洗掉浮色,才能看清真正染上的颜色。表面上看起来会变淡,可如果舍不得染料或是心急不洗的话,颜色看起来上得快,但掉得也快。”
虽然明白这个道理,我还是难以想象,从浅蓝到深蓝再到黑色,需要一个月里每天三次来做这件事。
“会太辛苦吗?”“不会,”黄奶奶回答:“染布高兴。”
3 喜悦从何而来
离开望谟县后,我经常穿着黄奶奶送我的布衣,总是会感到喜悦。衣服上散发着蓝靛的香气,棉布如同云团把我包围。这些都能拉回我浮游四处的注意力,感受身体被全然接纳。和黄奶奶相处的片段一幕幕浮现,也明白了染布对她来说并不是一项工作,而是生活本身,就像一日三餐和呼吸那样自然。日复一日的染布,也是透过染缸澄清内心。
记得有天染布时我问她:“你心里在想什么?”“什么也不想。”
那么我的喜悦从何而来?是因为我们的情谊吗?是奶奶的手作、传统款式,还是因为棉布、蓝染?还有我一开始想要到望谟追寻的问题:它们和我平时穿的衣服究竟有何根本不同,传承手艺的意义何在?
我想我的喜悦源自黄奶奶为衣服赋予的东西,如果仅仅把它称为爱或温情的话,未免太过笼统,它给我带来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会生出接受不确定的未来的勇气。
对制衣人来说,她们如举行仪式般专注着染布、成衣,或许也在这个过程中积攒起许多专注和深情。一位有十几年经验的阿姐曾告诉我:“做这衣服要有一颗温柔的心。”听时深深一颤,而用黄奶奶朴素的话,则是“染布高兴”。
力量、专注、当下和深情,是我们在现代社会向往寻获的东西,它们对人与万物来说至关重要。
作者:伍娇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