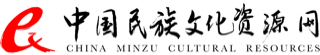发挥传统文化对生态资源的维护价值
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许多民族地区地处大江大河上游,是中华民族的生态屏障,开发资源一定要注意惠及当地、保护生态,做到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保护好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本钱。

贵州省锦屏县三江镇清水江沿岸,杉林茂盛。杨文斌摄
一、生态系统与文化的内在关联
人类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特殊性在于人类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
就生物性而言,人类是普通的生物物种,必须依赖自然生态系统,从中获取物质和能量。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不是直接与自然生态系统发生关系,而是在其特有文化的规约下,有意识地加工、改造和利用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从而建构起一个个互有区别的次生生态系统。这些次生生态系统已不再是纯自然生态系统,而是文化干预的产物。
文化干预体现了人类的社会属性,也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的本质区别之一。由于具有这样的社会属性,人类在能动地加工、改造和利用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或手段是可以选择和变化的。但是,自然生态系统不会任由文化干预,它自有一套运行规律,如果人类的文化行为可与之兼容,则二者趋向耦合,逐渐形成稳定延续的“文化生态”共同体;一旦人类的文化行为不能与之兼容,甚至超越其所能承受的范围,这种冲突就会以生态灾变的形式暴露出来,人类自身的生存繁衍也将受到威胁。显然,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是一种寄生并存的关系,人类的文化行为会伴随相应的生态后果。
历史地理学认为,人类的生活环境是经常变化的。这里所说的生活环境其实包括两种类型——自然的和人为的。在自然界作用下引发的生态系统改性的确存在,但在人类的生命周期内很难察觉,甚至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其变化都是非常微小的。恩格斯曾强调:“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
在这里,笔者想讨论的是人为作用下的生态变化。当今我们所看到的生态环境,并非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今天的山西长治已经不再是《茶经》中所说上等人参的主产地,毛乌素沙漠也不再是两晋时期水草丰茂、“未有若斯之美”的地方……不可否认,自然界对人类的作用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类的发展,但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凭借其文化力量改变了自然环境。
二、借鉴传统文化维护生态资源的智慧
人类对生态资源进行加工、改造和利用,以满足其生存、繁衍与发展的需要。人类对生态资源的利用,意味着对其不断地消耗。如果不能确保生态资源的可再生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就不能化解利用与消耗之间的矛盾,生态资源终有一天会耗尽。对生态资源的保护,可以在一段时期内、一定程度上限制人们的过度利用或不当行为,但如果保护仅是限制使用,就无法解决利用与消耗之间的根本矛盾,还需要对生态资源加以维护,才能实现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屏障功能。对此,我们要积极借鉴各民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观念,解决可持续利用生态资源这一现实问题。
生活在贵州清水江流域的侗族群众,60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杉树人工营林传统。杉树,属松科,常绿乔木,其原生地位于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高寒山区。清水江流域属于低山丘陵地带,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气候温暖潮湿,并不利于杉树林生长。然而,当地侗族先民将杉树移植至此,不仅使其存活下来,还带来了人工营林业的繁荣。历史上,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极为兴盛,这正是得益于当地民众经过不断的经验积累,逐步形成的一套完整、成熟、有效的“林粮间作”技术系统。
人工营林与自然林有本质区别。自然林是原生生态系统的产物,无需人工干预或管护,只要实施封山育林,其生态系统自然会稳定运行。人工营林则不然,由于其树种大多已脱离原生生态系统,植物在异地生长多有不适,最大的问题就是易感染病虫害,甚至引发生态灾变,需要不断地投入人力、技术去精心维护。比如,在“林粮间作”技术系统中的管护环节,林农们并不像现代林业产业那样仅种植单一树种,而是一般保存15%以上的其他树种活立木,特别是会为杉树配种其原生地的壳斗科树种,剔除当地与杉树发生强烈化感效应的樟科、芸香科乔木。通过这样的仿生种植,利用物种之间的制衡作用,杉树林染病虫害的风险可以降到最低程度。在杉木育林中,频繁使用“火焚”和搭配适量的伴生树种,不是孤立的技术表现,而是共同服务于病虫害防治、化解化感效应的有效措施。正如当地侗族群众所说,杉树林是护出来的,这样才有源源不断的木材。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吕洞山镇黄金村所在地山高坡陡,地质灾害隐患严重。但是,黄金村原生生态系统结构完整、层次丰富,地表植被覆盖率接近100%,原本的生态隐患都隐而不显,水土流失几乎无法被观察到。其河谷坡面的保水能力极强,历史上很少发生季节性干旱或山体滑坡等严重地质灾害。这样的生态系统,是依靠当地的苗族先民维护出来的。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苗族先民们逐渐积累起一套规避生态脆弱环节、维护生态资源的生计模式,他们在林中搭配种植藤蔓类或匍匐类植物,如葛藤。如果藤蔓植物长势过快,干扰高大乔木的生长,他们并不会将其清除,而是在间伐的时候,把藤条从乔木上拿开。这样既不会影响乔木生长,也不会妨碍藤蔓植物的生长。套种藤蔓类和匍匐类植物,主要是利用其对裸露基岩的遮蔽效果,以防止太阳直射基岩导致的高温,也可抑制水资源的无效蒸发,确保基岩和土层不会终年暴露在阳光之下和地表径流的冲刷下,以满足直立植物的正常生长需要。在当地人看来,这类植物浑身是宝,藤条纤维可用作布料,花可作蜜源,叶、果可用作家畜饲料,地下块根可作粮食。有一段时期,当地大规模引种玉米,将藤蔓植物清除,导致部分基岩和土壤裸露,一旦遭逢暴雨袭击,表土就会被不断冲刷走,严重时连种上的玉米也会被冲刷到河谷底部。如遇连续晴天,强烈的阳光不仅会炙烤玉米幼苗,还会导致水分蒸发,水土流失严重,甚至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事实证明,生态资源与民族文化是相互依存、共生共养的。如果割裂或者忽视他们之间的这种依附关系,生态环境就会恶化。
人类本身就置身于千差万别的文化系统和生态系统之中。不同的民族文化蕴含着大量丰富的本土生态知识和生存智慧,是人类取之不尽的宝库。要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本土生态知识,引导人们选择适宜的资源利用方式,保证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避免人为生态灾变的发生,从而维护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生态资源维护的价值研究》(项目号19XMZ105)成果。】
作者:皇甫睿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