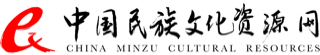怒族社会制度
怒族在很久以前即已形成以父家长为主的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但同时,原始的氏族、家族以及村落公社仍然不同程度的保存着。有些地区如碧江原第九行政村、普乐乡、老母登乡则还比较显著地保存着氏族组织和图腾崇拜,氏族血缘纽带还起着维系整个氏族共同利益的作用;福贡木古甲、固泉等村的怒族则还明显地保存父系大家族组织,一个村落基本上是由一个父系家族组成的;有些村落如知子罗、老母登、普乐、果课等则是由几个不同的氏族及家族组成的,这样便形成了许多村落公社。
怒江怒族村寨不论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公社,或以地缘为纽带的农村公社,个体家庭已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单位。如碧江九村的10个家族公社,每个公社都包括10至20户的个体家庭。公社有家族长,称“阿沙”,后来的村社长也沿用这一名称。阿沙不是正式选举产生的,一般都以辈分较高、有威信、受尊敬的长者担任,职责为处理公社内外公共事务,调解成员间的纠纷。阿沙通常兼作公社中的巫师,主持宗教祭祀。
家族之上的氏族,在怒族社会里只是名义上的存在,并只有一些残余现象。碧江怒语称氏族为“起”,福贡怒语称氏族为“休戚”,贡山怒语称氏族为“勒”,即同一个始祖所传的后裔都可称为一个氏族。氏族保有一些图腾名称,各个氏族对于他们的氏族图腾都有各种不同的传说。碧江原第九行政村四个家族分属两个氏族,一个蜂氏族叫“斗霍”,另一个虎氏族叫“达霍”。这两个氏族在历史上有密切关系,还残留有共同的祭祀崇拜仪式。氏族中实行父子连名制,其形式与今日大小凉山彝族及元阳县哈尼族的父子连名制相同。斗霍氏族能追溯到四十一代祖先的名字,约一千年的历史。但贡山、福贡两县的怒族没有氏族图腾与父子连名制,在社会组织、生活习俗上与碧江怒族都有一些差异。
各个家族公社或村社,基本上是一个独立单位,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家族公社碧江怒语称之为“谷”,福贡怒语称之为“体康”,即为同一父系祖先所传的后裔所形成的一个共同体。如碧江第九行政村“斗霍”“达霍”两个氏族之下又分为“俄皮谷”“俄哈谷”“俄则谷”“俄衣谷”等四个父系大家族;福贡木古甲乡努族的“仆纳庆”氏族之下又分为“次邦”“谷乃比”“夏鄂”“拉腾”“西子里”等五个“体康”。村落公社碧江怒语称之为“坑”,贡山怒语称之为“克恩”。村落公社作为一个社会和经济的组织,它具有下列特征:各个村社都根据山岭、溪谷等作为疆界,每一个村社一般包括两个以上的不同氏族和不同家族的成员组成,其他成员迁入村社内居住必须征得村社头人的同意,村社成员通过共同占有耕地,互相协作,共同承担这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义务而密切联结在一起;村社成员享有自由开垦共有荒地、捕猎野兽和采集野菜的权利,有共同的节日和习惯法准则,祭祀共同的山灵和树神,政治上是由各氏族和家族长组成临时性的“村社会议”,共同推选一个首领担任村社头人。
历史上曾有过氏族或村寨联盟,如在遇到人身伤害或重大敌对行为时,受害的一方可以“血族复仇”的方式向对方发出木刻,通知举行械斗,具有血缘亲族关系的同一氏族、同一家族甚至同一村落的成员都有义务参加械斗。此时如遇有整个氏族、家族的行动,则往往以血族友好的几个氏族或家族结成暂时性的军事联盟,来共同抵御敌方。如1880年至1900年间,福贡木古甲、固泉、木楞三村曾联合起来,与傈僳族发生过四次较大的械斗事件,但事后这种联盟也就解体了,表明家族、村社之上还没有产生过永久性的组织。
1912年前,怒族内部除了氏族及村社头人“阿沙”之外,还有维西康普、叶枝土司(纳西族)委派的伙头。这些伙头大都是原来的氏族、村社的头人。1908年,清官员夏瑚为了消除土司的影响,重新委派一批怒、傈僳族头人充当“怒管”或伙头,但各“怒管”、伙头仍然互不相属,照旧是一些以村社为单位的独立小集团。1912年云南地方政府的殖边队进驻怒江后,建立了行政委员公署,并从1914年起逐步实行保甲制度,把原来的怒管、伙头委任为乡、保、甲长,原来较为分散的“怒管”及伙头制度逐渐被统一在保甲制度下。
基督教传入后,某些信仰基督教的氏族、村社头人又成为教会的“马”(传教士)或“密枝扒”,这样又形成了政治和宗教两位一体的头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