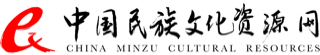民族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定义是:“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盈利的永久性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这一定义表明了博物馆对人类遗产负有特殊的使命,博物馆的机构性质决定了它对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责任,博物馆通过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和展出文化遗产来实现“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宗旨,也决定了它将在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中负有重要职责。无形文化遗产是整个文化遗产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博物馆自然应将其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
中国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只是提法有别,是以“少数民族的活文化”来表述的。“活文化”实际上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自20世纪30年代起,一些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就已经开始致力于这方面的收集和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随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各民族、地域的文化融合也在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如何保持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已成为全球诸多学术领域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在这一大环境下,我国逐渐兴起了一个保护、研究、发掘、抢救和收藏民族文化遗产的热潮,保护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从最初的学者呼吁,变为从政府各部门、学者、到民间组织及个人广泛参与、高度重视的文化活动。作为以收藏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为主要职能的博物馆,对此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尤其是民族(民俗)类博物馆,更应该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力军。
一、民族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中国的民族类博物馆,其雏形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华西大学、厦门大学,以及抗战时由上海内迁到贵阳的大夏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校,在当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并收集少数民族文物。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识别各少数民族,政府成立民族调查组,分赴各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有关专家有意识地收集民族、民间的遗物,包括少数民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服饰、宗教用品、文化用品、民间工艺品等。在此基础上,相关单位及民族院校纷纷成立民族文物室,后来陆续发展为民族博物馆,如民族文化宫、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博物馆。这是国内最早的一批民族类博物馆,它们与各院校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分不开。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增强,各民族地区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博物馆,如云南民族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馆、凉山彝族博物馆等。这些民族类博物馆,从诞生起就以收集、整理、保护和研究少数民族民间文化遗物为己任。
已故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吴泽霖先生说:“民族博物馆在今天的中国,指的是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一种专业性博物馆。”他把民族博物馆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民族博物馆,主要任务是“兄弟民族的实情介绍和民族政策的广泛宣传”;另一类是民族学博物馆,它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依附民族学而存在,其研究对象与民族学大体相同。民族学博物馆的研究在纵的方向:从事研究人们共同体,从家庭、氏族、部落和民族的发展规律;横的方向,从客观和微观的观点研究世界上有代表性的民族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不仅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而且要把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汉族和世界民族方面。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的重要研究手段,田野调查和文物收集,也是民族学博物馆建馆的重要基础。[1]
杨群在《民族学概论》中说:“搜集、保管、研究和陈列各种民族文物,是世界各国民族学无论哪个流派都普遍重视的科学工作,并为此而设立了各种各样的民族学博物馆或专门性的地志博物馆……收藏并研究民族文物是民族学和博物馆共同的重要任务。”他还认为:“凡是能够反映各族社会生活、如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艺术娱乐、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的古今实物资料,都属于民族文物。”而对于无法搬移的和属于精神文化范畴的文物,“如住宅、墓葬、节日歌舞、喜庆丧葬、宗教仪式、生活、自然风光、地理环境等,也应该尽量采取复制模型、绘画、摄影、录像、录音等手段,将原貌保存下来,入藏到博物馆内。”[2]而作为中国第一家以“民族学”命名的“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其最早的规划图,就是把南方具有代表意义的建筑以复制的方式,搬移至该博物馆周围,作为该博物馆的室外展览,并招录本民族传统艺人在该民族建筑内进行现场展示。这与如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某些思路不谋而合,可惜由于经费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最终没能实现。
关于民族博物馆的主要职能,民族学家杨堃先生曾说:“民族学博物馆,它是搜集与陈列世界各民族文物资料的场所与研究机构” ,“民族学博物馆的主要任务,便是对于民族文物的搜集、整理、展览、维修、保存和研究” 。此外,“还要研究这类博物馆的建筑设计、行政管理、业务领导和文物交换等项工作。”[3]
可见,不论从成立背景,还是职能发挥,民族博物馆都与民族文物保护紧密相连。民族文物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离不开物质,物质是文化的载体,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实际上是不能够分割开来单独谈的,二者结合才能够完整。就如一件文物,如果没有文化背景资料,其价值就大打折扣。文化也一样,离开了物质谈文化,文化就变成了空中楼阁,成为抽象、空洞的纯精神领域的东西。可以说,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都是按照一定的价值观(包括使用价值、精神价值、审美价值等)去制作使用的,所有的物态产品中都寓含着文化价值观。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离开物质载体是不可能产生的,也不可能存在。负载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物态系统,我们称之为传承物,也就是民族文物。民族文物与一般文物的区别在于,一般文物包括遗址和遗物,是指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装饰物及建筑遗址等,也包括墓葬的随葬品及画像砖、甲骨、简牍、钱币等,这些遗物都经过人类有意识的加工和使用,负载着制作者和使用者的历史文化信息。民族文物习惯上是指少数民族文物,它除了一般意义的文物涵盖的内容外,还包含“民族学文物”或“民族学标本”。这种文物不一定具有历史性,是近现代的产品,是近现代民族生活中的使用物,但它负载着某一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凡是能够体现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生产生活传承物,都可能成为博物馆和专门机构的收藏物、展示物。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大量生产生活传承物,虽不是文物,但具有“文物性”,随着被确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相关的传承物意义发生重大转变,生成了博物馆收藏、展示、研究的价值。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物应采取与“可移动文物”相类比的保护措施。此外,伴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承物的还有一种保护形势是“活态保护”。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一些具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能继续活态保护的,如赫哲族的鱼皮衣,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的狍皮帽、桦树皮制品,黎族、傣族的文身等,对这些只能进行“静态保护”,通过文字资料、音像资料等方式记录。
收藏、展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可移动文物”及有重大价值的“传承物”,是民族博物馆的一项重要职能。在今后的民族博物馆建设中,应当大力加强这一职能。
二、民族博物馆从成立以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就
民族博物馆自产生以来,除了在传统博物馆的收藏、展示、保护、修复和研究民族文物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首先是抢救和保护了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博物馆搜集到各类民族文物20000多件。在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区,其省级博物馆一般都专门设立有民族文物组,其中云南省博物馆和内蒙古博物馆搜集民族文物各有5000余件,广西民族博物馆收集民族文物20000余件。在各地的民族高等院校的博物馆,也收集了不少民族文物,如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有民族文物30000余件,中南民族大学有10000余件,西南民族大学有民族文物10000余件,另外在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有10000余件包括东南亚各国以及台湾地区各民族的文物,还有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也有2000余件民族文物以及大量的图片和影像资料。此外,北京的民族文化宫也藏有相当数量的民族文物。这些民族文物,承载了大量的民族文化遗产的信息,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4]
其次是最早利用拍照、摄像等方法,记录了一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20世纪50至60年代,我国有关部门曾在全国进行工艺美术大普查,恢复了不少濒临失传的工艺技术,并从老艺人那里记录下了许多传统的工艺,采取文字记录、图画、记谱、录音和照相等方法,成功抢救、挖掘和保存了不少濒临灭绝的民间文化。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些民族学工作者用影视方法及时地“如实记录”了当时独龙族、怒族、佤族、景颇族等民族中保存的各种“原始社会文化现象”。到1965年,仅以云南民族志为题,共拍摄专题记录片20余部。[5]据统计,现今在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中,收藏了反映我国20世纪20至60年代的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照片250余幅,反映世界各地历史文化的人类学电影和记录片800余部。还有各民族院校博物馆收藏的有关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图片和音像资料,20世纪60年代以前收集的资料,其中保存的文化信息,如今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文化现象已经消失。这实际上是早期的民族学博物馆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不自觉的保护。
再次是利用博物馆的有利宣传展示方式,通过复原场景、幻影成像、多媒体播放等先进技术方式,保护、宣扬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博物馆的展示方式有了新的突破,改变了以往把文物独立分开、单件摆放的展示手法,而是充分发掘文物背后的文化信息,复原文物的历史文化背景,把文物与历史文化背景相结合。这种展示手段,在民族类博物馆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民族文物如果脱离了文化背景,就完全失去了它的价值。如黎族的钻木取火,留下的遗物只有几段很普通的小木棍,无论从材质还是外观,都很难显示它的价值来,但如果利用场景复原,或幻影成像技术,则可以把黎族原始的取火方式再现给观众,使观众犹如身临其境,过而不忘。现在新建的民族民俗类博物馆几乎都采用了这种方法,如北京的中华民族博物馆,复制了16个民族村(又名民族分馆),分别按照藏、苗、傣、赫哲等民族的特色建筑风格而建,在各族建筑内,按照本民族的习惯摆放物件,举行节庆活动。这实际上是把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搬进了博物馆。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要想原地原貌保存少数民族的活态文化,是不现实的,虽然可以短暂人为控制,但终究不是长久之策。而这种把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搬进博物馆的做法却是切实可行的。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新展览,也利用了场景复原和多媒体等技术来展示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效果很好。
三、民族博物馆保护、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法与手段
对于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根据无形文化的特点,制定合适的保护原则,采取合乎其特点的保护措施。目前,博物馆界讨论的方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采用录音、摄像等多媒体技术,进行“记忆”保存;二是传承、延续,使其永保活力。比较而言,前者更容易,而后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非博物馆一家之力所能完成,要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够使无形文化遗产永久传承下去。
1.博物馆要建立起一套无形文化遗产的调查、收集、保护、研究、整理、建档的方法和规划,并投入一定的人力和物力,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工艺、有杰出艺术价值的民间口头文学、突出代表民族传统文化的无形遗产,都要建立无形文化遗产档案,开展抢救性保护措施。
2.把无形文化遗产物化、有形化,收入博物馆永久保存。无形文化遗产虽然属于精神领域的,但它也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能够被感知,它要表现出来就必须具有物质形式。博物馆可以通过对无形文化遗产的物化,来进行保护和收藏,如采用录音、摄像等多媒体技术,进行视频、音频的信息采集,然后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处理,制作成多媒体光碟等,光碟也是无形遗产的一种物化品,可以作为有形资料永久保存。
3.对于传承和发扬,一是要对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二是要广泛的宣传,使后辈认识其重要价值,主动自愿地承担起传承人的角色。
4.利用博物馆的优势环境,多种手段宣传和展示无形文化遗产。传统博物馆大多采用封闭式的静态展示,静态展览适合于藏品珍贵的历史博物馆,而以民族民俗文物为主的博物馆则更适合动态展示。所谓动态展示,就是在三维立体展陈环境里,观众可以接触展品,并参与操作,加强观众与藏品的亲近感,拉近观众与博物馆的距离,使博物馆的展览更加直观、真实,从而加强观众对展品的印象。在新建的民族民俗类博物馆中,这种展示手段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这类博物馆中,展览目的是要展示各民族的民俗现象,揭示展品蕴涵的民俗文化。只有采用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方法,才能够更有效地展示各民族文化。如何能够使民族文物在展览中活起来,可以通过高科技手段,利用声、光、电、影等,模拟真实场景,采用蜡像、沙盘、微缩景观等形式,动态地反映民俗实情。这种展示方式,一定要注意真实性、原始性,尽量少加粉饰,保持原汁原味。
5.利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展示无形文化遗产。随着我国数字博物馆的建立,实体博物馆有了更广泛的发展空间。人们可以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随地参观网上的博物馆,它有着实体博物馆无法比拟的优势,如利用虚拟空间,将文化遗产文字化、图形化、音像化,制作模拟场景,把真实的历史搬入虚拟的网络博物馆;数字博物馆还可以不受资金、场地限制,随时更新内容。现实中无法活态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在数字博物馆中永久“活”着。
6.利用生态博物馆整体保护文化遗产,让文化遗产在现实中永久地传承下去。生态博物馆是作为对传统博物馆保护文化遗产的缺陷的一种补偿而出现的,它强调人类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的整体保护。从1995年开始建立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开始,到现在,中国已先后在贵州、广西、内蒙古等地建立了苗族、布依族、汉族、侗族、瑶族、蒙古族等7座生态博物馆,绝大部分都建立在民族地区。作为一种新兴的博物馆形态和“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社会活标本”,生态博物馆就是原封不动地把整座村寨连同居民的习俗进行整体保护。生态博物馆经过10多年的历程,在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方面,特别是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具有传统博物馆不可替代的优势。然而,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外界文化的不断冲击,生态博物馆到底能够保持多久,还有待观察,如何解决永久性保持生态博物馆内居民的原生态文化与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这一矛盾,成为生态博物馆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吴泽霖:《论博物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民族文物工作通讯》,1985年第4期。
[2] 杨群:《民族学概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30—131页。
[3] 杨堃:《谈谈民族博物馆学》,《民族文物工作通讯》,1985年第2期。
[4] 本组数字引用自《中国博物馆指南》。
[5] 吕建昌:《博物馆与当代社会若干问题的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
引自:《中国民族文博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