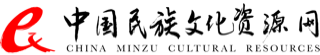梯田书写的记忆片断
A
一群研究哈尼(阿卡)学的西方学者,坐在一辆大巴车上。溜·格索是其中的一个。当车窗外出现云南元阳老虎嘴那一泄万丈的梯田时,他的嘴慢慢张大了。终于,车里有人大喊:停车!
车子停下。于是,涌下车去的几十位老外学者,对着山下那一片不可思议的哈尼梯田,大呼小叫。
我的丈夫——在那次第一届国际哈尼/阿卡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他担任翻译——从溜·格索那里听到了西方学者对于梯田毫不吝惜的赞美。他们说:这简直是世界第七大奇观啊!然后,他把老外们对于哈尼梯田不同寻常的反应,转述给自己的哈尼同胞。
中国的哈尼学者们那时是什么表情呢?我猜,史军超老师一定是若有所思。
这是20年前的事。
B
一张小小的照片,黑白的。我盯着它看。惊叹!心跳,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看哪,那密密麻麻的梯田!那万万千千条田埂,那丝丝缕缕、无边无际的线条!那整个天地仿佛只剩下了它们,梯田!
哈尼梯田太浩大壮美了,生命不过是它的小小过客!在建水县红河民族研究所的办公室里,我放下那张小小的黑白照片,喘了一口气。
“给我们杂志写篇稿子吧,关于哈尼梯田。”我对在场的哈尼学者黄绍文说。
几个月后,黄绍文的稿子寄到北京。我所做的事,是把这篇学术文章改成一篇稍带情感色彩的报道性文字;然后,为它琢磨一个让人动容的标题。“哈尼梯田:若干世纪里的生命与血汗。”对,就是它了!然后,我决定让那张小小的黑白照片铺满整整一个版面。
这是1996年第1期《民族团结》杂志。
出刊一个星期,《中国日报》的一位编辑来到杂志社,商谈翻译并转载这篇文章的事情。几天后,我就看到了占据《中国日报》整整一个版面的哈尼梯田的英文图文。
若干年后,我确认自己做了一件事:第一次在全国性新闻媒体上,大规模报道哈尼梯田。
这是18年前的事。
C
史军超老师提出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我在心中击节:多么伟大、高妙的创意啊!
电话采访史军超老师。然后,他寄来了一篇手书的自述。
我决定写一篇关于哈尼梯田“申遗”的文章,寄给《北京青年报》。那时我这样想:做个试验吧——用哈尼梯田做一个关于少数民族话题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市场主流媒体所接受的试验!
当然,做试验得慎重选材。选择哈尼梯田,是因为我以为这道风景足够结实,足够伟大,足够袭人耳目。把它交给主流媒体!看吧,炙手可热的主流媒体在那撼天撼地的景观面前作何反应?
我等待。直到有一天,那张整个版面充满哈尼梯田文字与图片的报纸出来。
一个成功的试验!——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一家主流媒体的明智,还是说明哈尼梯田的魅力?然而后者,还需要证明吗?
不论怎样,当哈尼梯田正式宣布“申遗”后,我在互联网上发现:上千个网页转载了这篇文章。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当哈尼梯田首次成为大众传媒关注的话题时,我为众多读者提供了关于哈尼梯田的启蒙性信息。
对了,记得我给红河州委宣传部寄去了那张报纸,并写了一封短信:
“将这张报纸寄来,是为了作一个纪念:哈尼梯田征服了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或许,它还会是一个见证:哈尼梯田终有一天将成为舆论的热点,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重读这封短信时,心里颇有些得意——看啊,我在十数年前就作出了一个预言!
但事实上,史军超老师的预言,比我的要震撼多了。找出他寄来的自述,我重新读到了这段文字:
“我的家乡红河,有一个巨大的事件正在悸动着、发展着,它的影响远不止于哈尼一个民族和元阳一个县份,它将牵系到红河州400万人的生存和发展,甚至还将波及到整个滇南地域的变迁。”
看啊,他用那么充满力量、睿智又具有诗的华丽神彩的语言,预言了发生在今天的事情!
而那是12年前的事。
D
张红榛有一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从她接受哈尼梯田“申遗”任务的那一天起,她就豪迈地说:“申遗不成功,绝不剪辫子!”
张红榛从此在某种意义上就为梯田而活了。
我见证她的努力。她来北京了,找各种各样的专家。她又来北京了,争取各级领导的重视。她再来北京了,开座谈会,请一批媒体去认识哈尼梯田……红河州哈尼梯田管理局局长张红榛忙得在天上飞来飞去。
我见证她的焦灼。或者是在我的家里,或者是在北京的某个旅馆里,或者是在云南的某个梯田文化保护座谈会上,她把这个问题翻来覆去跟我讨论来又讨论去:哈尼梯田如何更快地“申遗”?
我见证她的蜕变。那些年,每当有机会跟她在一起时,我会努力向她传递一个理念:“申遗”的目的,并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在于向世界传播哈尼梯田的文化价值。后来,她来过一封信,是这样说的:“‘申遗’工作不知不觉走了近十年,犹如老牛爬坡,进展不甚理想。但我认为,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它教会我们许多。如果说,我们曾经迫切地渴望世界遗产的金字招牌,那么现在,我们在不放弃的前提下,更追求本地区的和谐发展;如果说曾经偏重扩大知名度的宣传,现在则更关注当地百姓的宣传教育。这里有你说过的文化自觉,也有人文的关怀!”老实说,读到这封信时,我心里多么欣慰啊!赶紧拿起电话,对那边的红榛说:“恭喜,你已经真正成为了哈尼梯田的守护者——是这项文化遗产灵魂的守护者,而不仅仅是它形貌的守护者!”我的声音很有点矫情,但其实,是充满了深情:“红榛,你现在是哈尼梯田的守护神!”我说。
红榛的辫子还有多粗?我问从红河来的朋友。
“细了,又细了。你想,年纪大了,又那么累,还不整天掉头发?”朋友念叨。
辫子从粗到细。张红榛从焦灼到从容。从以“申遗”为职守,到以唤起哈尼人的文化自觉为神圣使命。
这是过去整整12年间的事。
E
事实上,自从提出哈尼梯田“申遗”的那一天起,史军超就为梯田而活了。
他建构了“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哈尼梯田意义阐释系统;他原创“中国人工湿地经典”的梯田理论。
也就是说,他让世界知道:哈尼梯田绝不只是一道取悦于人眼的风光造物。
在学术沙场上,他已经突破了很多很多阵地了。但是,他还得面对很多很多难题:在一个现代性一阵阵紧叩哀牢山的时代里,前现代性的农业文化,还能够维持多久?梯田如此古老,它如何接纳现代化?
也就是说,作为哈尼梯田文化价值的主要阐释者,史军超最后必须得说清楚这件事——现代化与梯田,可以鱼与熊掌,二者兼得?
我一趟趟跟进史老师的理论突破。用文字记录他的学术行进史。我知道,我必然会以一个记者的姿态,等候在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处——这个问题就埋伏在他理论路上的最后一道壕堑: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双重紧逼下,梯田文化如何完成自主转型?如何为梯田文化找到新的普世价值?
说这个问题紧要,是因为如果回答不了它,那么梯田即便“申遗”成功,命运又会怎样?
那次我赶到红河州驻京办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在一个子夜时分,我听他宣判哈尼梯田的未来命运——一个关于梯田的自觉的文化重构行动纲领。
我当然地记录并报道了这一个行动纲领。很高兴——我能够在纷纷扬扬的思想大雾里,见证一个理念的尘埃落定。我为这个也许会在未来展开的理想写下这样的导语:
“哈尼梯田成为世界性话语的深刻意义,在于它反映了一个民族文化自觉的历程——一种偏居一隅的文化传统,在基于清醒的自我观照后,于全球化时代所作的命运选择与自主重构。它隐含了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在全球化浪潮的拍岸声中,我们能够把握民族文化转型的自主权吗?我们能够为自己的民族找到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和坐标吗?我们能够激发出古老传统的原创力吗?”
从1998年第一次慷慨激奋地提出哈尼梯田“申遗”,到面对如此沉重的梯田现代性命题,这条路多长啊!
不久前的一个早晨,手机响了,打开来,便读到了短信:
“庆安与郑茜弟妹如握:久未联络,殊有念焉。6月17日至27日,余将以专家组长身份参加中国代表团赴柬埔寨联合国世界遗产大会,红河哈尼梯田将在此次会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哈尼民族为此大业奋斗凡十余载,梦想终获成真,此中亦有二位心血在,特与小友分享也!军超大哥”。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在心里说。等啊等,等了多久啊!
那是过去整整15年的事情。
F
无意间,我用文字,卷入了与哈尼梯田相关的一系列当代文化事件。
哈尼梯田在文字里向我展现它的意义。从它的视觉震撼,到它的当代困惑;从它所隐含的文化悖论,到它正在完成的文化重构。
说起梯田来,我已经是那样会心。我热衷于在朋友面前谈起它,因为我与天边的那一道风景已经是混得很熟的老朋友了。我知道很多关于它的家底它的故事,所以我总是喜欢在别人面前津津有味地谈起它。
但事实上,对于哈尼梯田而言,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过客;对于哈尼梯田“申遗”的过程而言,我只是一个从头到尾的见证者。
“今天中午1点20分正式通过哈尼梯田申遗成功。记下历史。有您的功劳!”一位红河的朋友发来短信。
“祝贺祝贺,哈尼梯田成为世界遗产了!”丈夫的导师、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来了电话。
下午三点之前,已经有两家媒体向我约稿。
“恭喜哈尼梯田申遗成功!”又有一位朋友发来短信。
我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
这是今天。我相信,此刻正在柬埔寨世界遗产大会现场的史军超和张红榛,一定眼含热泪。或者,已经泪流满面了。
这是公元2013年6月22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