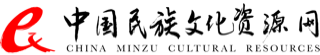2017年终特稿⑤民族文学 民族文学:在民族化底蕴中呈现更多“当代性”
在当前多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学必须与时代对话,构建出独特的文学经验世界,发现时代肌理深处所蕴含的丰富“民族化”质地,寻觅世道人心的“民族化”表达,否则文学的“民族性”面临着被消解和被剥夺修辞性的危机。但文学对民族性的过度渲染,又容易陷入民族话语自足性的窠臼,制掣着中华审美精神的整体性构建进程。因此,在二者之间寻找适度的言说区间,是少数民族文学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2017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尤其以小说为代表,在坚持以民族化叙事直抵、观照人性的同时,愈加呈现出高度自觉的民族文学话语主体性,也让民族小说叙事所思考的范围走向深广,整体呈现出极具本土化和民族化底蕴的“当代性”。
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困境,在个体人物与社会整体的互塑关系中挖掘人生悲剧的深层肌理
少数民族小说常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诗意、浪漫、温情、自守成为突出的艺术标签。但主体性自觉使少数民族作家开始将生命感知的触角深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将命运困厄与自我救赎作为小说叙事的基点。2017年的小说中,蕴涵着对生命、人心、人性的高贵与尊严的咏叹讴歌,始终秉持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
陶丽群(壮族)的《打开一扇窗子》中,民族习俗的“残忍”与生命亲情的“呵护”之间的表象错位,捍卫着跨越生死界限的人对未来的希冀;阿郎(藏族)的《簪花》,将日常生活对人的巨大牵制和裹挟力量尖锐地呈现出来;格致(满族)的《虎啸图》中,主人公在机关日常生活中,发现暗藏的权力机制,不仅入侵了个人生活,甚至主宰着个人身体与心灵的全部隐私;袁冰玮(满族)的《暴风雪》中,由自然界的暴风雪给主人公的身体所造成的伤害,延伸到掩藏于平凡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看似阳光明媚、实则冰冷残酷的心灵之霜;阿舍(维吾尔族)的《吉日》,从主人公的青春眼眸中折射出芸芸众生努力生活却遭生活戏谑的悲凉和荒诞,勾勒出碎片、庸常、异化的日常生活的别样质地。在许连顺(朝鲜族)的《女儿六岁初长成》、梁志玲(壮族)的《噪音》等作品中,日常生活中的女性或母亲,承载着来自男权社会、家庭变故或者社会底层的压抑、边缘化与孤独,隐藏着对性别主体处境的隐忧。
马金莲(回族)的《旁观者》和《听见》,在温婉的叙事中充盈着强烈的社会批判和生存叩问;光盘(瑶族)的《重回梅山》,在爷爷的回忆录和“我”的现实亲历交织中,在理想与欲望、良知谴责和资本贪婪的对比当中,完成了一个反生活逻辑的精神反思;陈思安(蒙古族)的《大娘》中,李铁军因替友复仇心切而求助于地下江湖组织,非理性的行径实则是现代法律程序和社会公权力缺失之后的艰难和无奈;杨芳兰(侗族)的《跃龙门》中,李兰香和杨明珠经历着城市底层生存的艰辛、屈辱和不堪,但努力与拼搏的结果却是始料未及的集资骗局和人际戏弄,资本欲望攫取了民族信仰的自守,在无尽的欲望助澜之下,明珠陷入了丧失本我的泥淖中无法自拔,唯有最质朴的亲情才是命运波澜的可靠港湾;图尔逊·买合木提(维吾尔族)的《沙村人家》中,4位热心公益人士的善举却遭受到村人的无端指责、误解和污蔑,小说饱含着对社会普遍流行的猜忌和丑陋世风浸染下人性卑劣的批判。
对历史与当下的双重反思和身份建构
2017年的少数民族小说,除了对抗日战争等主流历史进行整理,更执著于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解密。
昳岚(达斡尔族)的《雅德根》,跨越了满洲国至今的近百年历史,在达斡尔族的民俗展览中,勾连起以苏如勤为典型的萨满世家几代人的生命链,定格着一段久远的民族文化记忆;益希单增(藏族)的《困惑的年代》,在回溯金沙江边农奴制度所造成的苦难历史中,发出了历史可能重演的危机预言;刘荣书(满族)的《纪念碑》,提出了“当下,我们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英雄、对待历史”的严肃命题;白崇人(回族)的《瓷枕》,在黄大有对祖辈辉煌历史功勋的追叙中,凸显出历史如何进入当下生活的难题;句芒云路(苗族)的《手语》,勾勒出一幅神秘历史的招魂图景,隐喻着对民族根祖的辉煌与逝去的喟惋;第代着冬(苗族)的《口信像古歌流传》,从民族口信拓展出由不同人物勾连出的宏大历史;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的《草原骑士》,复现出一幕幕草原民族鲜活而丰富的历史生活场景;乌雅泰(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和他的两匹骏马》,更是一部将学术文献和文学想象相融合、致敬蒙古族先祖成吉思汗的历史寻根文本。
宗教信仰在人的精神生活中呈现坚定、放逐或救赎的诸多形态,成为2017年少数民族小说所集体抒写的文化瞻望。
信仰具有心灵救赎的超越功能。王华(仡佬族)的《陈泊水的救赎之路》中,陈泊水一系列荒诞古怪和匪夷所思的日常行为,是对自我罪恶的积极救赎,这是他在人生暮年的唯一出路;木兰(侗族)的《白光灼灼》中,郭小惠因年轻时追求非理性的复仇快感而诬陷别人,后她婚姻破裂、母子分别、锒铛入狱,救赎不仅是精神忏悔,更是世俗受难;野海(土家族)的《菩萨看得起人》将陈老三的杀戮与佛心并置,境遇的巨大反差呈现出的是对人的本质性的重观,蕴含着对精神单纯性、心灵圣洁性的守望;扎巴(藏族)的《飞扬的风马旗》对佛教与世俗的救赎之艰难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信仰具有与世俗制衡的幽冥神性。郭雪波(蒙古族)的《那根结有疙瘩的攀绳》,将宗教轮回和人性本能转换为跌宕离奇的世俗玄机,而破解世道人心的密匙则是人类无法预知的萨满教的牛性神祇;丁颜(回族)的《蓬灰》中,索菲亚在日常生活的喧嚣中仍能葆有对精神净地的守护,这种对超越性的追求折射出另类生命体验;尹向东(藏族)的《猎手》演绎出人性至善的艰难觉醒。
信仰具有批判沉沦的隐喻功能。夏鲁平(满族)的《棒槌谣》中,能够通灵的萨满获得了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超越性理解,这是对人性之劣的一种反证式批判;格绒追美(藏族)的《格萨尔王出山记》,将活佛、说唱艺人、英雄传奇放置于现代社会的网络媒体、现代都市和大众文化等同一时空,传奇英雄主义与世俗消费人生的相遇,在反衬出历史英雄精神逝去的苍凉之时,更烛照出当代社会人性迷失的苍白。
在对人的存在姿态的审视中,实现本土化叙事构建
2017年的少数民族小说,是对民族本土生活的深刻眷恋,回归成为个体安置漂浮灵魂的寓居方式。关仁山(满族)的《金谷银山》描绘的是新时代的乡村建设图,乡村重新成为人的理想和希望的飞地;向本贵(苗族)的《花垭人家》展示出人与大地永恒的生命关联;金革(朝鲜族)的《骨头》中,寿根记忆中唯一的故乡渐行渐远,也代表着情感家园最后的湮没;冯昱(瑶族)的《割树脂的人》,在对城市化发展的不自信当中,将乡土视为最后的栖居之地;何鸟(彝族)的《玩笑不分真假》中,何老左对土地的固守和眷恋,隐含着对城市化进程导致的人的“失根”状态的警惕;彭绪洛(土家族)的《兰草谷历险记》中,对世外桃源的向往更是将乡土想象极度地浪漫化和诗意化;梦非(羌族)的《半怀往事》对本族生活的“传奇”演绎,构造出一个迥异于农耕与都市景观的前现代生活图景;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蒙古族)的《逐狼呼和塔拉》中对呼伦贝尔大草原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诗性叙事,超越了简单的人性批判,将对乡土的守望上升到世间万物的生命彼此相依的共同体意识层面。
另一方面,2017年的少数民族小说秉持都市现代化合法性的价值立场,即对民族本土生活的理性批判,逃离成为保障个体自由的方式。杨仕芳(侗族)的《望云岭》,演绎的是乡村道德对人性尊严和生命权利戕害的悲剧;在俄狄小丰(彝族)的《萨河情事》中,逃离萨河包办婚姻的理想之所,竟然是大都市广州的自由和宽容;卢应江(苗族)的《星星和霓虹》将城乡对立的问题推向前台,母亲与女儿对城市充满恐惧和沉溺的态度,蕴含着对本土生活变革动力的理性审视与情感迷茫。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作家在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抉择中,常将这一根本性命题转换为“逃离和归乡之间的无所适从”“理性启蒙和情感依恋的两难境地”。在袁仁琮(侗族)的《支撑》中,内雅为了让子女实现身份的蜕变,将他们送去大学和城市之后,自己却忍受着心灵的孤独;潘年英(侗族)的《哭嫁歌》,以老东回寨子参加外甥女婚礼的系列场景为主线,本土生活的消逝、文化传统的尴尬,一切都在褪去了和谐、秩序和庄重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夹击下,走向老东难以理解的“现代”;杨胜应(苗族)的《普通话》,同样将本土与外在的区隔问题置于叙事核心,不讲普通话无法在城市当中与他人交流或找到工作,讲普通话却又遭到本乡群体的鄙视与排斥——语言不仅是基本的表述工具,在这里已经是身份认同的表征符号,逃离或回归的抉择已经很难将这种区隔彻底消除。
回顾2017年,少数民族文学承接着民族话语与时代生活进行嫁接、介入和对话的突围方向,并逐步表现出愈加显著的主体性自觉。民族叙事开始走出自足性的认知和美学范畴,并就救赎、压抑、批判、坚守等人类精神的共通性命题,表达着民族化的文学理解方式。与此同时,以民族传统文化来充实当代思想,依托民族美学的彰显与反思来构建文学的当代性,2017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仍然面临着文学经验系统化的整体焦虑。期待2018年!